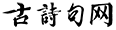《水浒传》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
作者:施耐庵
古风一首: 宋朝运祚将倾覆,四海英雄起寥廓。流光垂象在山东,正罡上应三十六。
瑞气盘旋绕郓城,此乡生降宋公明。神清貌古真奇异,一举能令天下惊。
幼年涉猎诸经史,长为吏役决刑名。仁义礼智信皆备,曾受九天玄女经。
江湖结纳诸豪杰,扶危济困恩威行。他年自到梁山泊,绣旗影摇云水滨。
替天行道呼保义,上应玉府天魁星。
话说宋江在酒楼上与刘唐说了话,分付了回书,送下楼来。刘唐连夜自回梁山泊去了。只说宋江乘着月色满街,信步自回下处来。一头走,一面肚里想:“那晁盖却空教刘唐来走这一遭。早是没做公的看见,争些儿露出事来。”走不过三二十步,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声押司。宋江转回头来看时,却是做媒的王婆,引着一个婆子,却与他说道:“你有缘,做好事的押司来也。”宋江转身来问道:“有甚么话说?”王婆拦住,指着阎婆对宋江说道:“押司不知,这一家儿从东京来,不是这里人家。嫡亲三口儿。夫主阎公,有个女儿婆惜。他那阎公平昔是个好唱的人,自小教得他那女儿婆惜也会唱诸般耍令。年方一十八岁,颇有些颜色。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,流落在此郓城县。不想这里的人,不喜风流宴乐。因此不能过活。在这县后一个僻净巷内权住。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。这阎婆无钱津送,停尸在家,没做道理处。央及老身做媒。我道这般时节,那里有这等恰好。又没借贷处。正在这里走头没路的。只见押司打从这里过来,以此老身与这阎婆赶来。望押司可怜见他则个,作成一具棺材。”宋江道:“原来恁地。你两个跟我来。”去巷口酒店里,借笔砚写过帖子,“与你去县东阵三郎家,取具棺材。”宋江又问道:“你有结果使用吗?”阎婆答道:“实不瞒押司说,棺材尚无,那讨使用。其实缺少。”宋江道:“我再与你银子十两做使用钱。”阎婆道:“便是重生的父母,再长的爹娘。做驴做马。报答押司。”宋江道:“休要如此说。”随即取出一锭银子,递与阎婆,自回下处去了。且说这婆子将了贴子,迳来县东街陈三郎家,取了一具棺材,回家发送了当,兀自余剩下五六两银子。娘儿两个把来盘缠,不在话下。忽一朝,那阎婆因来谢宋江,见他下处没有一个妇人家面。回来问间壁王婆道:“宋押司下处不见一个妇人面,他曾有娘子也无?”王婆道:“只闻宋押司家里在宋家村住,不曾见说他有娘子。在这县里做押司,只是客居。常常见他散施棺材药饵,极肯济人贫苦。敢怕是未有娘子。”阎婆道:“我这女儿长得好模样,又会唱曲儿,省得诸般耍笑。从小儿在东京时,只去行院人家串。那一个行院不爱他。有几个上行首,要问我过房几次,我不肯。只因我两口儿无人养老,因此不过房与他。不想今来到苦了他。我前日去谢宋押司,见他下处无娘子,因此央你与我对宋押司说:“他若要讨人时,我情愿把婆惜与他。我前日得你作成,亏了宋押司救济,无可报答他。与他做个亲眷来往。”王婆听了这话,次日来见宋江,备细说了这件事。宋江初时不肯。怎当这婆子撮合山的嘴,撺掇宋江依允了。就在县西巷内,讨了一所楼房,置办些家火什物,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那里居住。没半月之间,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,遍体金玉。正是:
花容袅娜,玉质娉婷。髻横一片乌云,眉扫半弯新月。金莲窄窄,湘裙微露不胜情。玉笋纤纤,翠袖半笼无限意。星眼浑如点漆,酥胸真似截肪。韵度若风里海棠花,标格似雪中玉梅树。金屋美人离御苑,B547珠仙子下尘寰。 宋江又过几日,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。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。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。向后渐渐来得慢了。却是为何?原来宋江是个好汉,只爱学使枪棒,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。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,况兼十八九岁,正在妙龄之际,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。一日,宋江不合带后司贴书张文远来阎婆惜家吃酒。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。那厮唤做小张三,生得眉清目秀,齿白唇红。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,飘蓬浮荡,学得一身风流俊俏,更兼品竹弹丝,无有不会。这婆惜是个酒色倡妓,一见张三,心里便喜,倒有意看上他。那张三见这婆惜有意,以目送情。等宋江起身净手,倒把言语来嘲惹张三。常言道:“风不来,树不动。舡不摇,水不浑。”那张三亦是个酒色之徒,这事如何不晓得。因见这婆娘眉来眼去,十分有情,记在心里。向后宋江不在时,这张三便去那里,假意儿只做来寻宋江。那婆娘留住吃茶。言来语去,成了此事。谁想那婆娘自从和那张三两个搭识上了,打得火块一般热。亦且这张三又是个惯弄此事的。岂不闻古人之言,“一不将,二不带。”只因宋江千不合,万不合,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,以此看上了他。自古道:“风流茶说合,酒是色媒人。”正犯着这条款。阎婆惜是个风尘倡妓的性格,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答上了,他并无半点儿情分在那宋江身上。宋江但若来时,只把言语伤他,全不兜揽他些个。这宋江是个好汉胸襟,不以这女色为念。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。那张三和这婆惜,如胶似漆,夜去明来。街坊上人也都知了。却有些风声吹在宋江耳朵里。宋江半信不信。自肚里寻思道:“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。他若无心恋我,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。我只不上门便了。”自此有个月不去。阎婆惜累使人来请,宋江只推事故,不上门去。忽一日晚间,却好见那阎婆赶到县前来,叫道:“押司,多日使人相请。好贵人难见面。便是小贱人有些言语高低,伤触了押司,也看得老身薄面,自教训他与押司陪话。今晚老身有缘得见押司,同走一遭去。”宋江道:“我今日县里事务忙,摆拨不开,改日却来。”阎婆道:“这个使不得。我女儿在家里,专望押司,胡乱温顾他便了。直恁地下得!”宋江道:“端的忙些个。明日准来。”阎婆道:“我今晚要和你去。”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,发话道:“是谁挑拨你?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,都靠着押司。外人说的闲是闲非,都不要听他。押司自做个张主。我女儿但有差错,都在老身身上。押司胡乱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:“你不要缠,我的事务分拨不开在这里。”阎婆道:“押司便误了些公事,知县相公不到得便责罚你。这回错过,后次难逢。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。到家里自有告诉。”宋江是个快性的人,乞那婆子缠不过,便道:“你放了手,我去便了。”阎婆道:“押司不要跑了去,老人家赶不上。”宋江道:“直恁地这等!”两个厮跟着来到门前。有诗为证:
酒不醉人人自醉,花不迷人人自迷。直饶今日能知悔,何不当初莫去为。
宋江立住了脚。阎婆把手一拦,说道:“押司来到这里,终不成不入去了!”宋江进到里面凳子上坐了。那婆子是乖的。自古道:“老虔婆,如何出得他手。”只怕宋江走去,便帮在身边坐了。叫道:“我儿,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。”那阎婆惜倒在床上,对着盏孤灯,正在没可寻思处,只等这小张三来。听得娘叫道:“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,”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,慌忙起来,把头掠一掠云髻,口里喃喃的骂道:“这短命等得我苦也!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。”飞也似跑下楼来。就隔子眼里张时,堂前琉璃灯却明亮,照见是宋江。那婆娘复翻身再上楼去了。依前倒在床上。阎婆听得女儿脚步下楼来了,又听得再上楼去了。婆子又叫道:“我儿,你的三郎在这里,怎地倒走了去?”那婆惜在床上应道:“这屋里不远,他不会来!他又不瞎,如何自不上来?直等我来迎接他。没了当絮絮聒聒地!”阎婆道:“这贱人真个望不见押司来,气苦了恁地说。也好教押司受他两句儿。”婆子笑道:“押司,我同你上楼去。”宋江听了那婆娘说这几句,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。被这婆子一扯,勉强只得上楼去。原来是一间六椽楼屋。前半间安一副春台卓凳,后半间铺着卧房,贴里安一张三面菱花的床,两边都是栏干,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。侧首放个衣架,搭着手巾,这边放着个洗手盆。一张金漆卓子上,放一个锡灯台。边厢两个杌子。正面壁上,挂一幅仕女。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。宋江来到楼上,净婆便拖入房里去。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床边坐了。阎婆就床上拖起女儿来,说道:“押司在这里。我儿,你只是性气不好,把言语伤触了他,恼得押司不上门。闲时恰在家里思量。我如今不容易请得他来,你却不起来陪句话儿,颠倒使性!”婆惜把手摔开,说那婆子:“你做甚么这般乌乱?我又不曾做了歹事。他自不上门,教我怎地陪话?”宋江听了,也不做声。婆子便掇过一把交椅,在宋江肩下,便推他女儿过来,说道:“你且和三郎坐一坐。不陪话便罢。不要焦燥。你两个多时不见,也说一句有情的话儿。”那婆娘那里肯过来。便去宋江对面坐了。宋江低了头不做声。婆子看女儿时,也别转了脸。阎婆道:“没酒没浆,做甚么道场。老身有一瓶儿好酒在这里,买些果品来与押司陪话。我儿,你相陪押司坐地,不要怕羞,我便来也。”宋江自寻思道:“我吃这婆子钉住了,脱身不得。等他下楼去,我随后也走了。”那婆子瞧见宋江要走的意思,出得房门去,门上却有屈戌,便把房门拽上,将屈戌搭了。宋江暗忖道:“那虔婆倒先算了我。”且说阎婆下楼来,先去灶前点起个灯,灶里见成烧着一锅脚汤,再辏上些柴头。拿了些碎银子,出巷口去买得些时新果子,鲜鱼嫩鸡肥鲊之类,归到家中,都把盘子盛了。取酒倾在盆里,舀半旋子,在锅里汤热了,倾在酒壶里。收拾了数盘菜蔬,三只酒盏,三双筋,一桶盘托上楼来,放在春台上。开了房门,搬将入来,摆在卓子上。看宋江时,只低着头。看女儿时,也朝着别处。阎婆道:“我儿起来把盏酒。”婆惜道:“你们自吃,我不耐烦。”婆子道:““我爷娘手里从小儿惯了你性儿,别人面上须使不得。”婆惜道:“不把盏便怎地我!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?”那婆子倒笑起来,说道:“又是我的不是了。押司是个风流人物,不和你一般见识。你不把酒便罢,且回过脸来吃盏儿酒。”婆惜只不回过头来。那婆子自把酒来劝宋江。宋江勉意吃了一盏。婆子道:“押司莫要见责,闲话都打迭起。明日慢慢告诉。外人见押司在这里,多少干热的不怯气,胡言乱语,放屁辣臊,押司都不要听。且只顾饮酒。”筛了三盏在卓子上,说道:“我儿不要使小孩儿的性,胡乱吃一盏酒。”婆惜道:“没得只顾缠我!我饱了,吃不得。”阎婆道:“我儿,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吃盏酒使得。”婆惜一头听了,一面肚里寻思:“我只心在张三身上,兀谁奈烦相伴这厮!若不把他灌得醉了,他必来缠我。”婆惜只得勉意拿起酒来,吃了半盏。婆子笑道:“我儿只是焦燥,且开怀吃两盏儿睡。押司也满饮几杯。”宋江被他劝不过,连饮了三五杯。婆子也连连吃了几盏。再下楼去烫酒。那婆子见女儿不吃酒,心中不悦。才见女儿回心吃酒,欢喜道:“若是今夜兜得他住,那人恼恨都忘了。且又和他缠几时,却再商量。”婆子一头寻思,一面自在灶前吃了三大钟酒,觉道有些痒麻上来。却又筛了一碗吃。旋了大半旋,倾在注子里,爬上楼来。见那宋江低着头不做声,女儿也别转着脸弄裙子。这婆子哈哈地笑道:“你两个又不是泥塑的,做甚么都不做声?押司,你不合是个男子汉,只得装温柔,说些风话儿耍。”宋江正没做道理处,口里只不做声,肚里好生进退不得。阎婆惜自想道:“你不来采我,指望我娘一似闲常时来陪你话,相伴你耍笑,我如今却不耍!”那婆子吃了许多酒,口里只管夹七带八嘈。正在那里张家长,李家短,白说绿道。有诗为证: 假意虚脾恰似真,花言巧语弄精神。几多伶俐遭他陷,死后应知拔舌根。
却有郓城县一个卖糟B548的的唐二哥,叫做唐牛儿,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,常常得宋江赍助他。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,也落得几贯钱使。宋江要用他时,死命向前。这一日晚,正赌钱输了,没做道理处,却去县前寻宋江。奔到下处寻不见。街坊都道:“唐二哥,你寻谁这般忙?”唐牛儿道:“我喉急了,要寻孤老。一地里不见他。”众人道:“你的孤老是谁?”唐牛儿道:“便是县里宋押司。”众人道:“我方才见他和阎婆两个过去,一路走着。”唐牛儿道:“是了。这阎婆惜贼贱虫,他自和张三两个打得火块也似热,只瞒着宋押司一个。他敢也知些风声,好几时不去了。今晚必然乞那老咬虫假意儿缠了去。我正没钱使,喉急了,乱去那里寻几贯钱使。就帮两碗酒吃。”一迳奔到阎婆门前。见里面灯明,门却不关。入到胡梯边,听的阎婆在楼上呵呵地笑。唐牛儿捏脚捏手,上到楼上。板壁缝里张时,见宋江和婆惜两个,都低着头。那婆子坐在横头卓子边,口里七十三八十四只顾嘈。唐牛儿闪将入来,看着阎婆和宋江、婆惜,唱了三个喏,立在边头。宋江寻思道:“这厮来的最好。”把嘴望下一努。唐牛儿是个乖的人,便瞧科。看着宋江便说道:“小人何处不寻过,原来却在这里吃酒耍。好吃得安稳!”宋江道:“莫不是县里有甚么要紧事?”唐牛儿道:“押司,你怎地忘了?便是早间那件公事,知县相公在厅上发作,着四五替公人来下处寻押司,一地里又没寻处。相公焦燥做一片。押司便可动身。”宋江道:“恁地要紧!只得去。”便起身要下楼。吃那婆子拦住道:“押司不要使这科段。这唐牛儿捻泛过来。你这精贼也瞒老娘!正是鲁般手里调大斧。这早晚知县自回衙去,和夫人吃酒取乐,有甚么事务得发作。你这般道儿,只好瞒魍魉。老娘手里说不过去。”唐牛儿便道:“真个是知县相公紧等的勾当。我却不会说谎。”阎婆道:“放你娘狗屁!老娘一双眼,却似琉璃葫芦儿一般。却才见押司努嘴过来,叫你发科。你倒不撺掇押司来我屋里,颠倒打抹他去。常言道:‘杀人可恕,情理难容。”这婆子跳起身来,便把那唐牛儿匹B070子只一叉,浪浪跄跄直从房里叉下楼来。唐牛儿道:“你做甚么便叉我?”婆子喝道:“你不晓得,破人买卖衣饭,如杀父母妻子。你高做声,便打你这贼乞丐!”唐牛儿钻将过来道:“你打!”这婆子乘着酒兴,叉开五指,去那唐牛儿脸上连打两掌,直B22D出帘子外去。婆子便扯帘子,撇放门背后,却把两扇门关上,拿拴拴了,口里只顾骂。那唐牛儿吃了这两掌,立在门前大叫道:“贼老咬虫不要慌!我不看宋押司面皮,教你这屋里粉碎。教你双日不着单日着。我不结果了你,不姓唐!”拍着胸,大骂了去。婆子再到楼上,看着宋江道:“押司没事采那乞丐做甚么!那厮一地里去搪酒吃,只是搬是搬非。这等倒街卧巷的横死贼,也来上门上户欺负人。”宋江是个真实的人,吃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,倒抽身不得。婆子道:“押司不要心里见责老身,只恁地知重得了。我儿和押司只吃这杯。我猜着你两个多时不见,以定要早睡。收拾了罢休。”婆子又劝宋江吃两杯,收拾杯盘下楼来,自去灶下去。宋江在楼上自肚里寻思说:“这婆子女儿和张三两个有事,我心里半信不信。眼里不曾见真实。待要去来,只道我村。况且夜深了,我只得权睡一睡。有看这婆娘怎地,今夜与我情分如何?”只见那婆子又上楼来,说道:“夜深了,我叫押司两口儿早睡。”那婆娘应道:“不干你事,你自去睡。”婆子笑下楼来,口里道:“押司安置。今夜多欢。明日慢慢地起。”婆子下楼来,收拾了灶上,洗了脚手,吹灭灯,自去睡了。却说宋江坐在杌子上,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时先来偎倚陪话,胡乱又将就几时。谁想婆惜心里寻思道:“我只思量张三。吃他揽了,却似眼中钉一般。那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时前来下气。老娘如今却不要耍。只见说撑船就岸,几曾有撑岸就船。你不来采我,老娘倒落得。”看官听说,原来这色最是怕人。若是他有心恋你时,身上便有刀剑水火也拦他不住,他也不怕。若是他无心恋你时,你便身坐在金银堆里,他也不采你。常言道:“佳人有意村夫俏,红粉无心浪子村。”宋江明是个勇烈大丈夫,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。这阎婆惜被那张三小意儿白依百随,轻怜重惜,卖俏迎奸,引乱这婆娘的心,如何肯恋宋江。当夜两个在灯下坐着,对面都不做声,各自肚里踌躇。却似等泥干掇入庙。看看天色夜深,只见窗上月光。但见:
银河耿耿,玉漏迢迢。穿窗斜月映寒光,透户凉风吹夜气。雁声嘹亮,孤眠才子梦魂惊。蛩韵凄凉,独宿佳人情绪苦。谯楼禁鼓,一更未尽一更催。别院寒砧,千捣将残千捣起。画檐间叮当铁马敲碎旅客孤怀;银台上闪烁清灯,偏照离人长叹。贪淫妓女心如铁,仗义英雄气似虹。
当下宋江坐在杌子上,睃那婆娘时,复地叹口气。约莫也是二更天气。那婆娘不脱衣裳,便上床去,自倚了绣枕,纽过身,朝里壁自睡了,宋江看了,寻思道:“可奈这贱人全不采我些个!他自睡了。我今日吃这婆子言来语去,央了几杯酒,打熬不得。夜深,只得睡了罢。”把头上巾帻除下,放在卓子上,脱下盖衣裳,搭在衣架上。腰里解下銮带,上有一把压衣刀和招文袋,却挂在床边栏干子上。脱去了丝鞋净袜,便上床去那婆娘脚后睡了。半个更次,听得婆惜在脚后冷笑。宋江心里气闷,如何睡得着。自古道:“欢娱嫌夜短,寂寞恨更长。”看看三更交半夜,酒却醒了。捱到五更,宋江起来,面桶里洗了脸,便穿了上盖衣裳,带了巾帻,口里骂道:“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!”婆惜也不曾睡着。听得宋江骂时,纽过身回道:“你不羞这脸!”宋江忿那口气,便下楼来。阎婆听得脚步响,便在床上说道:“押司且睡歇,等天明去。没来由起五更做甚么?”宋江也不应,只顾来开门。婆子又道:“押司出去时,与我拽上门。”宋江出得门来,就拽上了。忿那口气没出处,一直要奔回下处来。却从县前过,见一碗灯明。看时,却是卖汤药的王公,来到县前赶早市。那老儿见是宋江来,慌忙道:“押司如何今日出来得早?”宋江道:“便是,夜来酒醉,错听五鼓。”王公道:“押司必然伤酒,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。”宋江道:“最好。”就凳上坐了。那老子浓浓地奉一盏二陈汤,递与宋江吃。宋江吃了,蓦然想起道:“如常吃他的汤药,不曾要我还钱。我旧时曾许他一具棺材,不曾系得他。想起前日有那晁盖送来的金子,受了他一条在招文袋里。何不就与那老儿做棺材钱,教他欢喜?”宋江便道:“王公,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,一向不曾把得与你。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,把与你,你便可将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,放在家里。你百年归寿时,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。若何?”王公道:“恩主如常觑老汉,又蒙与终身寿具,老子今世报答不得押司,后世做驴做马报答官人。”宋江道:“休如此说。”便起背子前襟,去取那招文袋时,吃了一惊,道:“苦也!昨夜正忘在那贱人的床头栏干子上?我一时气起来,只顾走了,不曾系得在腰里。这几两金子直得甚么!须有晁盖寄来的那一封书,包着这金。我本是在酒楼上刘唐前烧毁了,他回去说时,只道我不把他来为念。正要将到下处来烧,又谁想王婆布施棺材,就成了这件事。一向蹉跎忘了。昨夜晚正记起来,又不曾烧得,却被这阎婆缠将我去。因此忘在这贱人家里床头栏干子上。我常时见这婆娘看些曲本,颇识几字。若是被他拿了,到是利害。”便起身道:“阿公休怪。不是我说谎。只道金子在招文袋里,不想出来得忙,忘了在家。我去取来与你。”王公道:“休要去取,明日慢慢的与老汉不迟。”宋江道:“阿公,你不知道。我还有一件物事做一处放着,以此要去取。”宋江慌慌急急,奔回阎婆家里来。正是:
合是英雄命运乖,遗前忘后可怜哉。循环莫谓天无意,酝酿原知祸有胎。
且说这阎婆惜听得宋江出门去了,扒将起来,口里自言语道:“那厮揽了老娘一夜睡不着。那厮舍脸,只指望老娘陪气下情。我不信你!老娘自和张三过得好,谁奈烦采你。你不上门来,倒好!”口里说着,一头铺被。脱下截袄儿,解了下面裙子,袒开胸前,脱下截衬衣。床面前灯却明亮,照见床头栏干子上拖下条紫罗銮带。婆惜见了,笑道:“黑三那厮乞B549不尽,忘了銮带在这里,老娘且捉了,把来与张三系。”便用手去一提,提起招文袋和刀子来。只觉袋里有些重。便把手抽开,望卓了上只一抖,正抖出那包金子和书来。这婆娘拿起来看时,灯下照见是黄黄的一条金子。婆惜笑道:“天教我和张三买物事吃。这几日我见张三瘦了,我也正要买些东西和他将息。”将金子放下,却把那纸书展开来。灯下看时,上面写着晁盖并许多事务。婆惜道:“好呀!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,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。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,单单只多你这厮。今日也撞在我手里!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,送一百两金子与你。且不要慌,老娘慢慢地消遣你。”就把这封书依原包了金子,还插在招文袋里。“不怕你教五圣来摄了去。”正在楼上自言自语,只听得楼下呀地门响。婆子问道:“是谁?”宋江道:“是我。”婆子道:“我说早哩,押司却不信要去。原来早了又回来。且再和姐姐睡一睡,到大明去。”宋江也不回话,一迳奔上楼来。那婆娘听得是宋江回来,慌忙把銮带、刀子、招文袋,一发卷做一块,藏在被里,紧紧地靠了床里壁,只做B35CB35C假睡着。宋江撞到房里,迳去床头栏干上取时,却不见了,宋江心内自慌。只得忍了昨夜的气,把手去摇那妇人道:“你看我日前的面,还我招文袋。”那婆惜假睡着,只不应。宋江又摇道:“你不要急燥,我自明日与你陪话。”婆惜道:“老娘正睡哩,是谁揽我?”宋江道:“你晓的是我,假做甚么?”婆惜纽转身道:“黑三,你说甚么?”宋江道:“你还了我招文袋。”婆惜道:“你在那里交付与我手里?却来问我讨。”宋江道:“忘了在你脚后小B54A干上。这里又没人来,只是你收得。”婆惜道:“呸!你不见鬼来!”宋江道:“夜来是我不是了。明日与你陪话。你只还了我罢。休要作耍!”婆惜道:“谁和你作耍!我不曾收得。”宋江道:“你先时不曾脱衣裳睡,如今盖着被子睡。以定是起来铺被时拿了。”婆惜只是不与。正是:
雨意云情两罢休,无端懊恼触心头。重来欲索招文袋,致使鸳帏血漫流。
只见那婆惜柳眉踢竖,星眼圆睁,说道:“老娘拿是拿了,只是不还你。你使官府的人,便拿我去做贼断。!”宋江道:“我须不曾冤你做贼。”婆惜道:“可知老娘不是贼哩。”宋江见这话,心里越慌,便说道:“我须不曾歹看承你娘儿两个。还了我罢。我要去干事。”婆惜道:“闲常也只嗔老娘和张三有事。他有些不如你处,他不该一刀的罪犯,不强似你和打劫贼通同。”宋江道:“好姐姐,不要叫!邻舍听得,不是耍处。”婆惜道:“你怕外人听得,你莫做不得。这封书老娘牢牢地收着。若要饶你时,只依我三件事便罢。”宋江道:“休说三件事,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。”婆惜道:“只怕依不得。”宋江道:“当行即行。敢问那三件事?”阎婆惜道:“第一件事,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,再写一纸任从我改嫁张三,并不敢再来争执的文书。”宋江道:“这个依得。”婆惜道:“第二件,我头上带的,我身上穿的,家里使用的,虽都是你办的,也委一纸文书,不许你日后来讨。”宋江道:“这个也依得。”阎婆惜道:“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。”宋江道:“我已两件都依你,缘何这件依不得?”婆惜道:“有那梁山泊晁盖送与你的一百两金子,快把来与我,我便饶你这一场天字第一号官司,还你这招文袋里的款状。”宋江道:“那两件到都依得。这一百两金子,果然送来与我,我不肯受他的,依前教他把了回去。若端的有时,双手便送与你。”婆惜道:“可知哩。常言道:“公人见钱,如蝇子见血。他使人送金子与你,你岂有推了转去的。这话却似放屁!做公人的,那个猫儿不吃腥?阎罗王面前,须没放回的鬼。你待瞒谁!便把这一百两金子与我,直得甚么!你怕是贼赃时,快溶过了与我。”宋江道:“你也须知我是老实的人,不会说谎。你若不信,限我三日,我将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与你。你还了我招文袋。”婆惜冷笑道:“你这黑三倒乖!把我一似小孩般捉弄。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,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,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。我这里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。你快把来,两相交割。”宋江道:“果然不曾有这金子。”婆惜道:“明朝到公厅上,你也说不曾有这金子。”宋江听了公厅两字,怒气起,那里按纳得住!睁着眼道:“你还也不还?”那妇人道:“你恁地狠,我便还你不迭!”宋江道:“你真个不还?”婆惜道:“不还,再饶你一百个不还?”若要还时,在郓城县还你。”宋江便来扯那婆惜盖的被。妇人身边却有这件物,倒不顾被,两手只紧紧地抱住胸前。宋江扯开被来,却见这銮带头正在那妇人胸前拖下来。宋江道:“原来却在这里。”一不做,二不休,两手便来夺。那婆娘那里肯放。宋江在床边舍命的夺,婆惜死也不放。宋江恨命只一拽,倒拽出那把压衣刀子在席子上。宋江便抢在手里。那婆娘见宋江抢刀在手,叫:“黑三郎杀人也!”只这一声,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。那一肚皮气正没出处,婆惜却叫第二声时,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,右手却早刀落。去那婆惜颡子上只一勒,鲜血飞出。那妇人兀自吼哩。宋江怕他不死,再复一刀,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。但见:
手到处青春丧命,刀落时红粉亡身。七魄悠悠,已赴森罗殿上。三魂渺渺,应归枉死城中。紧闭星眸,直挺挺尸横席上。半开檀口,湿津津头落枕边。小院初春,大雪压枯金线柳。寒生庾岭,狂风吹折玉梅花。三寸气在千般用,一日无常万事休。红粉不知归何处?芳魂今夜落谁家?
宋江一时怒起,杀了阎婆惜,取过招文袋,抽出那封书来,便就残灯下烧了。系上銮带,走出楼来。那婆子在下面睡,听他两口儿论口,倒也不着在意里。只听得女儿叫一声:“黑三郎杀人也!”正不知怎地,慌忙跳起来,穿了衣裳,奔上楼来。却好和宋江打个胸厮撞。阎婆问道:“你两口儿做甚么闹?”宋江道:“你女儿忒无礼,被我杀了。”婆子笑道:“却是甚么!便是押司生的眼凶,又酒性不好,专要杀人。押司,休取笑老身。”宋江道:“你不信时,去房里看。我真个杀了。”婆子道:“我不信。”推开房门看时,只见血泊里挺着尸首。婆子道:“苦也!却是怎地好?”宋江道:“我是烈汉,一世也不走。随你要怎地。”婆子道:“这贱人果是不好,押司不错杀了。只是老身无人养赡。”宋江道:“这个不防。即是你如此说时,你却不用忧心。我家岂无珍羞百味,只教你丰衣足食便了,快活过半世。”阎婆道:“恁地时,却是好也。深谢押司。我女儿死在床上,怎地断送?”宋江道:“这个容易。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与你,仵作行人入殓时,我自分付他来。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。”婆子谢道:“押司,只好趁天未明时讨具棺材盛了,邻舍街坊,都不要见影。”宋江道:“也好。你取纸笔来,我写个批子与你去取。”阎婆道:“批子也不济事。须是押司自去取,便肯早早发来。”宋江道:“也说得是。”两个下楼来。婆子去房里拿了锁钥,出到门前,把门锁了,带了钥匙。宋江与阎婆两个,投县前来。此时天色尚早未明,县门却才开。那婆子约莫到县前左侧,把宋江一把结住,发喊叫道:“有杀人贼在这里!”吓得宋江慌做一团,连忙掩住口道:“不要叫。”那里掩得住。县前有几个做公的,走将拢来看时,认得是宋江,便劝道:“婆子闭嘴。押司不是这般的人。有事只消得好说。”阎婆道:“他正是凶首。与我捉住,同到县里。”原来宋江为人最好,上下爱敬,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。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。又不信这婆子说。正在那里没个解救,却好唐牛儿托一盘子洗净的糟B54B,来县前赶趁。正见这婆子结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。唐牛儿见是阎婆一把纽结住宋江,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鸟气来,便把盘子放在卖药的老王凳子上,钻将过来,喝道:“老贼虫你做甚么结纽住押司?”婆子道:“唐二,你不要来打夺人去。要你偿命也!”唐牛儿大怒,那里听他说。把婆子手一拆,拆开了,不问事由,叉开五指,去阎婆脸上只一掌,打个满天星。那婆子昏撒了,只得放手。宋江得脱,往闹里一直走了。婆子便一把却纽结住唐牛儿,叫道:“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,你却打夺去了!”唐牛儿慌道:“我那里得知!”阎婆叫道:“上下!替我捉一捉杀人贼则个!不时,须要带累你们。”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,不肯动手。拿唐牛儿时,须不担阁。众人向前,一个带住婆子三四个拿住唐牛儿,把他横拖倒拽,直推进郓城县里来。古人云:“祸福无门,惟人自招。披麻救火,惹焰烧身。”正是:三寸舌为诛命剑,一张口是葬身坑。毕竟唐牛儿被阎婆结住,怎地脱身,且听下回分解。
瑞气盘旋绕郓城,此乡生降宋公明。神清貌古真奇异,一举能令天下惊。
幼年涉猎诸经史,长为吏役决刑名。仁义礼智信皆备,曾受九天玄女经。
江湖结纳诸豪杰,扶危济困恩威行。他年自到梁山泊,绣旗影摇云水滨。
替天行道呼保义,上应玉府天魁星。
话说宋江在酒楼上与刘唐说了话,分付了回书,送下楼来。刘唐连夜自回梁山泊去了。只说宋江乘着月色满街,信步自回下处来。一头走,一面肚里想:“那晁盖却空教刘唐来走这一遭。早是没做公的看见,争些儿露出事来。”走不过三二十步,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声押司。宋江转回头来看时,却是做媒的王婆,引着一个婆子,却与他说道:“你有缘,做好事的押司来也。”宋江转身来问道:“有甚么话说?”王婆拦住,指着阎婆对宋江说道:“押司不知,这一家儿从东京来,不是这里人家。嫡亲三口儿。夫主阎公,有个女儿婆惜。他那阎公平昔是个好唱的人,自小教得他那女儿婆惜也会唱诸般耍令。年方一十八岁,颇有些颜色。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,流落在此郓城县。不想这里的人,不喜风流宴乐。因此不能过活。在这县后一个僻净巷内权住。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。这阎婆无钱津送,停尸在家,没做道理处。央及老身做媒。我道这般时节,那里有这等恰好。又没借贷处。正在这里走头没路的。只见押司打从这里过来,以此老身与这阎婆赶来。望押司可怜见他则个,作成一具棺材。”宋江道:“原来恁地。你两个跟我来。”去巷口酒店里,借笔砚写过帖子,“与你去县东阵三郎家,取具棺材。”宋江又问道:“你有结果使用吗?”阎婆答道:“实不瞒押司说,棺材尚无,那讨使用。其实缺少。”宋江道:“我再与你银子十两做使用钱。”阎婆道:“便是重生的父母,再长的爹娘。做驴做马。报答押司。”宋江道:“休要如此说。”随即取出一锭银子,递与阎婆,自回下处去了。且说这婆子将了贴子,迳来县东街陈三郎家,取了一具棺材,回家发送了当,兀自余剩下五六两银子。娘儿两个把来盘缠,不在话下。忽一朝,那阎婆因来谢宋江,见他下处没有一个妇人家面。回来问间壁王婆道:“宋押司下处不见一个妇人面,他曾有娘子也无?”王婆道:“只闻宋押司家里在宋家村住,不曾见说他有娘子。在这县里做押司,只是客居。常常见他散施棺材药饵,极肯济人贫苦。敢怕是未有娘子。”阎婆道:“我这女儿长得好模样,又会唱曲儿,省得诸般耍笑。从小儿在东京时,只去行院人家串。那一个行院不爱他。有几个上行首,要问我过房几次,我不肯。只因我两口儿无人养老,因此不过房与他。不想今来到苦了他。我前日去谢宋押司,见他下处无娘子,因此央你与我对宋押司说:“他若要讨人时,我情愿把婆惜与他。我前日得你作成,亏了宋押司救济,无可报答他。与他做个亲眷来往。”王婆听了这话,次日来见宋江,备细说了这件事。宋江初时不肯。怎当这婆子撮合山的嘴,撺掇宋江依允了。就在县西巷内,讨了一所楼房,置办些家火什物,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那里居住。没半月之间,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,遍体金玉。正是:
花容袅娜,玉质娉婷。髻横一片乌云,眉扫半弯新月。金莲窄窄,湘裙微露不胜情。玉笋纤纤,翠袖半笼无限意。星眼浑如点漆,酥胸真似截肪。韵度若风里海棠花,标格似雪中玉梅树。金屋美人离御苑,B547珠仙子下尘寰。 宋江又过几日,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。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。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。向后渐渐来得慢了。却是为何?原来宋江是个好汉,只爱学使枪棒,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。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,况兼十八九岁,正在妙龄之际,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。一日,宋江不合带后司贴书张文远来阎婆惜家吃酒。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。那厮唤做小张三,生得眉清目秀,齿白唇红。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,飘蓬浮荡,学得一身风流俊俏,更兼品竹弹丝,无有不会。这婆惜是个酒色倡妓,一见张三,心里便喜,倒有意看上他。那张三见这婆惜有意,以目送情。等宋江起身净手,倒把言语来嘲惹张三。常言道:“风不来,树不动。舡不摇,水不浑。”那张三亦是个酒色之徒,这事如何不晓得。因见这婆娘眉来眼去,十分有情,记在心里。向后宋江不在时,这张三便去那里,假意儿只做来寻宋江。那婆娘留住吃茶。言来语去,成了此事。谁想那婆娘自从和那张三两个搭识上了,打得火块一般热。亦且这张三又是个惯弄此事的。岂不闻古人之言,“一不将,二不带。”只因宋江千不合,万不合,带这张三来他家里吃酒,以此看上了他。自古道:“风流茶说合,酒是色媒人。”正犯着这条款。阎婆惜是个风尘倡妓的性格,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答上了,他并无半点儿情分在那宋江身上。宋江但若来时,只把言语伤他,全不兜揽他些个。这宋江是个好汉胸襟,不以这女色为念。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。那张三和这婆惜,如胶似漆,夜去明来。街坊上人也都知了。却有些风声吹在宋江耳朵里。宋江半信不信。自肚里寻思道:“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。他若无心恋我,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。我只不上门便了。”自此有个月不去。阎婆惜累使人来请,宋江只推事故,不上门去。忽一日晚间,却好见那阎婆赶到县前来,叫道:“押司,多日使人相请。好贵人难见面。便是小贱人有些言语高低,伤触了押司,也看得老身薄面,自教训他与押司陪话。今晚老身有缘得见押司,同走一遭去。”宋江道:“我今日县里事务忙,摆拨不开,改日却来。”阎婆道:“这个使不得。我女儿在家里,专望押司,胡乱温顾他便了。直恁地下得!”宋江道:“端的忙些个。明日准来。”阎婆道:“我今晚要和你去。”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,发话道:“是谁挑拨你?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,都靠着押司。外人说的闲是闲非,都不要听他。押司自做个张主。我女儿但有差错,都在老身身上。押司胡乱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:“你不要缠,我的事务分拨不开在这里。”阎婆道:“押司便误了些公事,知县相公不到得便责罚你。这回错过,后次难逢。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。到家里自有告诉。”宋江是个快性的人,乞那婆子缠不过,便道:“你放了手,我去便了。”阎婆道:“押司不要跑了去,老人家赶不上。”宋江道:“直恁地这等!”两个厮跟着来到门前。有诗为证:
酒不醉人人自醉,花不迷人人自迷。直饶今日能知悔,何不当初莫去为。
宋江立住了脚。阎婆把手一拦,说道:“押司来到这里,终不成不入去了!”宋江进到里面凳子上坐了。那婆子是乖的。自古道:“老虔婆,如何出得他手。”只怕宋江走去,便帮在身边坐了。叫道:“我儿,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。”那阎婆惜倒在床上,对着盏孤灯,正在没可寻思处,只等这小张三来。听得娘叫道:“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,”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,慌忙起来,把头掠一掠云髻,口里喃喃的骂道:“这短命等得我苦也!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。”飞也似跑下楼来。就隔子眼里张时,堂前琉璃灯却明亮,照见是宋江。那婆娘复翻身再上楼去了。依前倒在床上。阎婆听得女儿脚步下楼来了,又听得再上楼去了。婆子又叫道:“我儿,你的三郎在这里,怎地倒走了去?”那婆惜在床上应道:“这屋里不远,他不会来!他又不瞎,如何自不上来?直等我来迎接他。没了当絮絮聒聒地!”阎婆道:“这贱人真个望不见押司来,气苦了恁地说。也好教押司受他两句儿。”婆子笑道:“押司,我同你上楼去。”宋江听了那婆娘说这几句,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。被这婆子一扯,勉强只得上楼去。原来是一间六椽楼屋。前半间安一副春台卓凳,后半间铺着卧房,贴里安一张三面菱花的床,两边都是栏干,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。侧首放个衣架,搭着手巾,这边放着个洗手盆。一张金漆卓子上,放一个锡灯台。边厢两个杌子。正面壁上,挂一幅仕女。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。宋江来到楼上,净婆便拖入房里去。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床边坐了。阎婆就床上拖起女儿来,说道:“押司在这里。我儿,你只是性气不好,把言语伤触了他,恼得押司不上门。闲时恰在家里思量。我如今不容易请得他来,你却不起来陪句话儿,颠倒使性!”婆惜把手摔开,说那婆子:“你做甚么这般乌乱?我又不曾做了歹事。他自不上门,教我怎地陪话?”宋江听了,也不做声。婆子便掇过一把交椅,在宋江肩下,便推他女儿过来,说道:“你且和三郎坐一坐。不陪话便罢。不要焦燥。你两个多时不见,也说一句有情的话儿。”那婆娘那里肯过来。便去宋江对面坐了。宋江低了头不做声。婆子看女儿时,也别转了脸。阎婆道:“没酒没浆,做甚么道场。老身有一瓶儿好酒在这里,买些果品来与押司陪话。我儿,你相陪押司坐地,不要怕羞,我便来也。”宋江自寻思道:“我吃这婆子钉住了,脱身不得。等他下楼去,我随后也走了。”那婆子瞧见宋江要走的意思,出得房门去,门上却有屈戌,便把房门拽上,将屈戌搭了。宋江暗忖道:“那虔婆倒先算了我。”且说阎婆下楼来,先去灶前点起个灯,灶里见成烧着一锅脚汤,再辏上些柴头。拿了些碎银子,出巷口去买得些时新果子,鲜鱼嫩鸡肥鲊之类,归到家中,都把盘子盛了。取酒倾在盆里,舀半旋子,在锅里汤热了,倾在酒壶里。收拾了数盘菜蔬,三只酒盏,三双筋,一桶盘托上楼来,放在春台上。开了房门,搬将入来,摆在卓子上。看宋江时,只低着头。看女儿时,也朝着别处。阎婆道:“我儿起来把盏酒。”婆惜道:“你们自吃,我不耐烦。”婆子道:““我爷娘手里从小儿惯了你性儿,别人面上须使不得。”婆惜道:“不把盏便怎地我!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?”那婆子倒笑起来,说道:“又是我的不是了。押司是个风流人物,不和你一般见识。你不把酒便罢,且回过脸来吃盏儿酒。”婆惜只不回过头来。那婆子自把酒来劝宋江。宋江勉意吃了一盏。婆子道:“押司莫要见责,闲话都打迭起。明日慢慢告诉。外人见押司在这里,多少干热的不怯气,胡言乱语,放屁辣臊,押司都不要听。且只顾饮酒。”筛了三盏在卓子上,说道:“我儿不要使小孩儿的性,胡乱吃一盏酒。”婆惜道:“没得只顾缠我!我饱了,吃不得。”阎婆道:“我儿,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吃盏酒使得。”婆惜一头听了,一面肚里寻思:“我只心在张三身上,兀谁奈烦相伴这厮!若不把他灌得醉了,他必来缠我。”婆惜只得勉意拿起酒来,吃了半盏。婆子笑道:“我儿只是焦燥,且开怀吃两盏儿睡。押司也满饮几杯。”宋江被他劝不过,连饮了三五杯。婆子也连连吃了几盏。再下楼去烫酒。那婆子见女儿不吃酒,心中不悦。才见女儿回心吃酒,欢喜道:“若是今夜兜得他住,那人恼恨都忘了。且又和他缠几时,却再商量。”婆子一头寻思,一面自在灶前吃了三大钟酒,觉道有些痒麻上来。却又筛了一碗吃。旋了大半旋,倾在注子里,爬上楼来。见那宋江低着头不做声,女儿也别转着脸弄裙子。这婆子哈哈地笑道:“你两个又不是泥塑的,做甚么都不做声?押司,你不合是个男子汉,只得装温柔,说些风话儿耍。”宋江正没做道理处,口里只不做声,肚里好生进退不得。阎婆惜自想道:“你不来采我,指望我娘一似闲常时来陪你话,相伴你耍笑,我如今却不耍!”那婆子吃了许多酒,口里只管夹七带八嘈。正在那里张家长,李家短,白说绿道。有诗为证: 假意虚脾恰似真,花言巧语弄精神。几多伶俐遭他陷,死后应知拔舌根。
却有郓城县一个卖糟B548的的唐二哥,叫做唐牛儿,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,常常得宋江赍助他。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,也落得几贯钱使。宋江要用他时,死命向前。这一日晚,正赌钱输了,没做道理处,却去县前寻宋江。奔到下处寻不见。街坊都道:“唐二哥,你寻谁这般忙?”唐牛儿道:“我喉急了,要寻孤老。一地里不见他。”众人道:“你的孤老是谁?”唐牛儿道:“便是县里宋押司。”众人道:“我方才见他和阎婆两个过去,一路走着。”唐牛儿道:“是了。这阎婆惜贼贱虫,他自和张三两个打得火块也似热,只瞒着宋押司一个。他敢也知些风声,好几时不去了。今晚必然乞那老咬虫假意儿缠了去。我正没钱使,喉急了,乱去那里寻几贯钱使。就帮两碗酒吃。”一迳奔到阎婆门前。见里面灯明,门却不关。入到胡梯边,听的阎婆在楼上呵呵地笑。唐牛儿捏脚捏手,上到楼上。板壁缝里张时,见宋江和婆惜两个,都低着头。那婆子坐在横头卓子边,口里七十三八十四只顾嘈。唐牛儿闪将入来,看着阎婆和宋江、婆惜,唱了三个喏,立在边头。宋江寻思道:“这厮来的最好。”把嘴望下一努。唐牛儿是个乖的人,便瞧科。看着宋江便说道:“小人何处不寻过,原来却在这里吃酒耍。好吃得安稳!”宋江道:“莫不是县里有甚么要紧事?”唐牛儿道:“押司,你怎地忘了?便是早间那件公事,知县相公在厅上发作,着四五替公人来下处寻押司,一地里又没寻处。相公焦燥做一片。押司便可动身。”宋江道:“恁地要紧!只得去。”便起身要下楼。吃那婆子拦住道:“押司不要使这科段。这唐牛儿捻泛过来。你这精贼也瞒老娘!正是鲁般手里调大斧。这早晚知县自回衙去,和夫人吃酒取乐,有甚么事务得发作。你这般道儿,只好瞒魍魉。老娘手里说不过去。”唐牛儿便道:“真个是知县相公紧等的勾当。我却不会说谎。”阎婆道:“放你娘狗屁!老娘一双眼,却似琉璃葫芦儿一般。却才见押司努嘴过来,叫你发科。你倒不撺掇押司来我屋里,颠倒打抹他去。常言道:‘杀人可恕,情理难容。”这婆子跳起身来,便把那唐牛儿匹B070子只一叉,浪浪跄跄直从房里叉下楼来。唐牛儿道:“你做甚么便叉我?”婆子喝道:“你不晓得,破人买卖衣饭,如杀父母妻子。你高做声,便打你这贼乞丐!”唐牛儿钻将过来道:“你打!”这婆子乘着酒兴,叉开五指,去那唐牛儿脸上连打两掌,直B22D出帘子外去。婆子便扯帘子,撇放门背后,却把两扇门关上,拿拴拴了,口里只顾骂。那唐牛儿吃了这两掌,立在门前大叫道:“贼老咬虫不要慌!我不看宋押司面皮,教你这屋里粉碎。教你双日不着单日着。我不结果了你,不姓唐!”拍着胸,大骂了去。婆子再到楼上,看着宋江道:“押司没事采那乞丐做甚么!那厮一地里去搪酒吃,只是搬是搬非。这等倒街卧巷的横死贼,也来上门上户欺负人。”宋江是个真实的人,吃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,倒抽身不得。婆子道:“押司不要心里见责老身,只恁地知重得了。我儿和押司只吃这杯。我猜着你两个多时不见,以定要早睡。收拾了罢休。”婆子又劝宋江吃两杯,收拾杯盘下楼来,自去灶下去。宋江在楼上自肚里寻思说:“这婆子女儿和张三两个有事,我心里半信不信。眼里不曾见真实。待要去来,只道我村。况且夜深了,我只得权睡一睡。有看这婆娘怎地,今夜与我情分如何?”只见那婆子又上楼来,说道:“夜深了,我叫押司两口儿早睡。”那婆娘应道:“不干你事,你自去睡。”婆子笑下楼来,口里道:“押司安置。今夜多欢。明日慢慢地起。”婆子下楼来,收拾了灶上,洗了脚手,吹灭灯,自去睡了。却说宋江坐在杌子上,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时先来偎倚陪话,胡乱又将就几时。谁想婆惜心里寻思道:“我只思量张三。吃他揽了,却似眼中钉一般。那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时前来下气。老娘如今却不要耍。只见说撑船就岸,几曾有撑岸就船。你不来采我,老娘倒落得。”看官听说,原来这色最是怕人。若是他有心恋你时,身上便有刀剑水火也拦他不住,他也不怕。若是他无心恋你时,你便身坐在金银堆里,他也不采你。常言道:“佳人有意村夫俏,红粉无心浪子村。”宋江明是个勇烈大丈夫,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。这阎婆惜被那张三小意儿白依百随,轻怜重惜,卖俏迎奸,引乱这婆娘的心,如何肯恋宋江。当夜两个在灯下坐着,对面都不做声,各自肚里踌躇。却似等泥干掇入庙。看看天色夜深,只见窗上月光。但见:
银河耿耿,玉漏迢迢。穿窗斜月映寒光,透户凉风吹夜气。雁声嘹亮,孤眠才子梦魂惊。蛩韵凄凉,独宿佳人情绪苦。谯楼禁鼓,一更未尽一更催。别院寒砧,千捣将残千捣起。画檐间叮当铁马敲碎旅客孤怀;银台上闪烁清灯,偏照离人长叹。贪淫妓女心如铁,仗义英雄气似虹。
当下宋江坐在杌子上,睃那婆娘时,复地叹口气。约莫也是二更天气。那婆娘不脱衣裳,便上床去,自倚了绣枕,纽过身,朝里壁自睡了,宋江看了,寻思道:“可奈这贱人全不采我些个!他自睡了。我今日吃这婆子言来语去,央了几杯酒,打熬不得。夜深,只得睡了罢。”把头上巾帻除下,放在卓子上,脱下盖衣裳,搭在衣架上。腰里解下銮带,上有一把压衣刀和招文袋,却挂在床边栏干子上。脱去了丝鞋净袜,便上床去那婆娘脚后睡了。半个更次,听得婆惜在脚后冷笑。宋江心里气闷,如何睡得着。自古道:“欢娱嫌夜短,寂寞恨更长。”看看三更交半夜,酒却醒了。捱到五更,宋江起来,面桶里洗了脸,便穿了上盖衣裳,带了巾帻,口里骂道:“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!”婆惜也不曾睡着。听得宋江骂时,纽过身回道:“你不羞这脸!”宋江忿那口气,便下楼来。阎婆听得脚步响,便在床上说道:“押司且睡歇,等天明去。没来由起五更做甚么?”宋江也不应,只顾来开门。婆子又道:“押司出去时,与我拽上门。”宋江出得门来,就拽上了。忿那口气没出处,一直要奔回下处来。却从县前过,见一碗灯明。看时,却是卖汤药的王公,来到县前赶早市。那老儿见是宋江来,慌忙道:“押司如何今日出来得早?”宋江道:“便是,夜来酒醉,错听五鼓。”王公道:“押司必然伤酒,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。”宋江道:“最好。”就凳上坐了。那老子浓浓地奉一盏二陈汤,递与宋江吃。宋江吃了,蓦然想起道:“如常吃他的汤药,不曾要我还钱。我旧时曾许他一具棺材,不曾系得他。想起前日有那晁盖送来的金子,受了他一条在招文袋里。何不就与那老儿做棺材钱,教他欢喜?”宋江便道:“王公,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,一向不曾把得与你。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,把与你,你便可将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,放在家里。你百年归寿时,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。若何?”王公道:“恩主如常觑老汉,又蒙与终身寿具,老子今世报答不得押司,后世做驴做马报答官人。”宋江道:“休如此说。”便起背子前襟,去取那招文袋时,吃了一惊,道:“苦也!昨夜正忘在那贱人的床头栏干子上?我一时气起来,只顾走了,不曾系得在腰里。这几两金子直得甚么!须有晁盖寄来的那一封书,包着这金。我本是在酒楼上刘唐前烧毁了,他回去说时,只道我不把他来为念。正要将到下处来烧,又谁想王婆布施棺材,就成了这件事。一向蹉跎忘了。昨夜晚正记起来,又不曾烧得,却被这阎婆缠将我去。因此忘在这贱人家里床头栏干子上。我常时见这婆娘看些曲本,颇识几字。若是被他拿了,到是利害。”便起身道:“阿公休怪。不是我说谎。只道金子在招文袋里,不想出来得忙,忘了在家。我去取来与你。”王公道:“休要去取,明日慢慢的与老汉不迟。”宋江道:“阿公,你不知道。我还有一件物事做一处放着,以此要去取。”宋江慌慌急急,奔回阎婆家里来。正是:
合是英雄命运乖,遗前忘后可怜哉。循环莫谓天无意,酝酿原知祸有胎。
且说这阎婆惜听得宋江出门去了,扒将起来,口里自言语道:“那厮揽了老娘一夜睡不着。那厮舍脸,只指望老娘陪气下情。我不信你!老娘自和张三过得好,谁奈烦采你。你不上门来,倒好!”口里说着,一头铺被。脱下截袄儿,解了下面裙子,袒开胸前,脱下截衬衣。床面前灯却明亮,照见床头栏干子上拖下条紫罗銮带。婆惜见了,笑道:“黑三那厮乞B549不尽,忘了銮带在这里,老娘且捉了,把来与张三系。”便用手去一提,提起招文袋和刀子来。只觉袋里有些重。便把手抽开,望卓了上只一抖,正抖出那包金子和书来。这婆娘拿起来看时,灯下照见是黄黄的一条金子。婆惜笑道:“天教我和张三买物事吃。这几日我见张三瘦了,我也正要买些东西和他将息。”将金子放下,却把那纸书展开来。灯下看时,上面写着晁盖并许多事务。婆惜道:“好呀!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,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。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,单单只多你这厮。今日也撞在我手里!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,送一百两金子与你。且不要慌,老娘慢慢地消遣你。”就把这封书依原包了金子,还插在招文袋里。“不怕你教五圣来摄了去。”正在楼上自言自语,只听得楼下呀地门响。婆子问道:“是谁?”宋江道:“是我。”婆子道:“我说早哩,押司却不信要去。原来早了又回来。且再和姐姐睡一睡,到大明去。”宋江也不回话,一迳奔上楼来。那婆娘听得是宋江回来,慌忙把銮带、刀子、招文袋,一发卷做一块,藏在被里,紧紧地靠了床里壁,只做B35CB35C假睡着。宋江撞到房里,迳去床头栏干上取时,却不见了,宋江心内自慌。只得忍了昨夜的气,把手去摇那妇人道:“你看我日前的面,还我招文袋。”那婆惜假睡着,只不应。宋江又摇道:“你不要急燥,我自明日与你陪话。”婆惜道:“老娘正睡哩,是谁揽我?”宋江道:“你晓的是我,假做甚么?”婆惜纽转身道:“黑三,你说甚么?”宋江道:“你还了我招文袋。”婆惜道:“你在那里交付与我手里?却来问我讨。”宋江道:“忘了在你脚后小B54A干上。这里又没人来,只是你收得。”婆惜道:“呸!你不见鬼来!”宋江道:“夜来是我不是了。明日与你陪话。你只还了我罢。休要作耍!”婆惜道:“谁和你作耍!我不曾收得。”宋江道:“你先时不曾脱衣裳睡,如今盖着被子睡。以定是起来铺被时拿了。”婆惜只是不与。正是:
雨意云情两罢休,无端懊恼触心头。重来欲索招文袋,致使鸳帏血漫流。
只见那婆惜柳眉踢竖,星眼圆睁,说道:“老娘拿是拿了,只是不还你。你使官府的人,便拿我去做贼断。!”宋江道:“我须不曾冤你做贼。”婆惜道:“可知老娘不是贼哩。”宋江见这话,心里越慌,便说道:“我须不曾歹看承你娘儿两个。还了我罢。我要去干事。”婆惜道:“闲常也只嗔老娘和张三有事。他有些不如你处,他不该一刀的罪犯,不强似你和打劫贼通同。”宋江道:“好姐姐,不要叫!邻舍听得,不是耍处。”婆惜道:“你怕外人听得,你莫做不得。这封书老娘牢牢地收着。若要饶你时,只依我三件事便罢。”宋江道:“休说三件事,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。”婆惜道:“只怕依不得。”宋江道:“当行即行。敢问那三件事?”阎婆惜道:“第一件事,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,再写一纸任从我改嫁张三,并不敢再来争执的文书。”宋江道:“这个依得。”婆惜道:“第二件,我头上带的,我身上穿的,家里使用的,虽都是你办的,也委一纸文书,不许你日后来讨。”宋江道:“这个也依得。”阎婆惜道:“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。”宋江道:“我已两件都依你,缘何这件依不得?”婆惜道:“有那梁山泊晁盖送与你的一百两金子,快把来与我,我便饶你这一场天字第一号官司,还你这招文袋里的款状。”宋江道:“那两件到都依得。这一百两金子,果然送来与我,我不肯受他的,依前教他把了回去。若端的有时,双手便送与你。”婆惜道:“可知哩。常言道:“公人见钱,如蝇子见血。他使人送金子与你,你岂有推了转去的。这话却似放屁!做公人的,那个猫儿不吃腥?阎罗王面前,须没放回的鬼。你待瞒谁!便把这一百两金子与我,直得甚么!你怕是贼赃时,快溶过了与我。”宋江道:“你也须知我是老实的人,不会说谎。你若不信,限我三日,我将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与你。你还了我招文袋。”婆惜冷笑道:“你这黑三倒乖!把我一似小孩般捉弄。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,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,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。我这里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。你快把来,两相交割。”宋江道:“果然不曾有这金子。”婆惜道:“明朝到公厅上,你也说不曾有这金子。”宋江听了公厅两字,怒气起,那里按纳得住!睁着眼道:“你还也不还?”那妇人道:“你恁地狠,我便还你不迭!”宋江道:“你真个不还?”婆惜道:“不还,再饶你一百个不还?”若要还时,在郓城县还你。”宋江便来扯那婆惜盖的被。妇人身边却有这件物,倒不顾被,两手只紧紧地抱住胸前。宋江扯开被来,却见这銮带头正在那妇人胸前拖下来。宋江道:“原来却在这里。”一不做,二不休,两手便来夺。那婆娘那里肯放。宋江在床边舍命的夺,婆惜死也不放。宋江恨命只一拽,倒拽出那把压衣刀子在席子上。宋江便抢在手里。那婆娘见宋江抢刀在手,叫:“黑三郎杀人也!”只这一声,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。那一肚皮气正没出处,婆惜却叫第二声时,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,右手却早刀落。去那婆惜颡子上只一勒,鲜血飞出。那妇人兀自吼哩。宋江怕他不死,再复一刀,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。但见:
手到处青春丧命,刀落时红粉亡身。七魄悠悠,已赴森罗殿上。三魂渺渺,应归枉死城中。紧闭星眸,直挺挺尸横席上。半开檀口,湿津津头落枕边。小院初春,大雪压枯金线柳。寒生庾岭,狂风吹折玉梅花。三寸气在千般用,一日无常万事休。红粉不知归何处?芳魂今夜落谁家?
宋江一时怒起,杀了阎婆惜,取过招文袋,抽出那封书来,便就残灯下烧了。系上銮带,走出楼来。那婆子在下面睡,听他两口儿论口,倒也不着在意里。只听得女儿叫一声:“黑三郎杀人也!”正不知怎地,慌忙跳起来,穿了衣裳,奔上楼来。却好和宋江打个胸厮撞。阎婆问道:“你两口儿做甚么闹?”宋江道:“你女儿忒无礼,被我杀了。”婆子笑道:“却是甚么!便是押司生的眼凶,又酒性不好,专要杀人。押司,休取笑老身。”宋江道:“你不信时,去房里看。我真个杀了。”婆子道:“我不信。”推开房门看时,只见血泊里挺着尸首。婆子道:“苦也!却是怎地好?”宋江道:“我是烈汉,一世也不走。随你要怎地。”婆子道:“这贱人果是不好,押司不错杀了。只是老身无人养赡。”宋江道:“这个不防。即是你如此说时,你却不用忧心。我家岂无珍羞百味,只教你丰衣足食便了,快活过半世。”阎婆道:“恁地时,却是好也。深谢押司。我女儿死在床上,怎地断送?”宋江道:“这个容易。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与你,仵作行人入殓时,我自分付他来。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。”婆子谢道:“押司,只好趁天未明时讨具棺材盛了,邻舍街坊,都不要见影。”宋江道:“也好。你取纸笔来,我写个批子与你去取。”阎婆道:“批子也不济事。须是押司自去取,便肯早早发来。”宋江道:“也说得是。”两个下楼来。婆子去房里拿了锁钥,出到门前,把门锁了,带了钥匙。宋江与阎婆两个,投县前来。此时天色尚早未明,县门却才开。那婆子约莫到县前左侧,把宋江一把结住,发喊叫道:“有杀人贼在这里!”吓得宋江慌做一团,连忙掩住口道:“不要叫。”那里掩得住。县前有几个做公的,走将拢来看时,认得是宋江,便劝道:“婆子闭嘴。押司不是这般的人。有事只消得好说。”阎婆道:“他正是凶首。与我捉住,同到县里。”原来宋江为人最好,上下爱敬,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。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。又不信这婆子说。正在那里没个解救,却好唐牛儿托一盘子洗净的糟B54B,来县前赶趁。正见这婆子结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。唐牛儿见是阎婆一把纽结住宋江,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鸟气来,便把盘子放在卖药的老王凳子上,钻将过来,喝道:“老贼虫你做甚么结纽住押司?”婆子道:“唐二,你不要来打夺人去。要你偿命也!”唐牛儿大怒,那里听他说。把婆子手一拆,拆开了,不问事由,叉开五指,去阎婆脸上只一掌,打个满天星。那婆子昏撒了,只得放手。宋江得脱,往闹里一直走了。婆子便一把却纽结住唐牛儿,叫道:“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,你却打夺去了!”唐牛儿慌道:“我那里得知!”阎婆叫道:“上下!替我捉一捉杀人贼则个!不时,须要带累你们。”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,不肯动手。拿唐牛儿时,须不担阁。众人向前,一个带住婆子三四个拿住唐牛儿,把他横拖倒拽,直推进郓城县里来。古人云:“祸福无门,惟人自招。披麻救火,惹焰烧身。”正是:三寸舌为诛命剑,一张口是葬身坑。毕竟唐牛儿被阎婆结住,怎地脱身,且听下回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