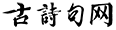《鸳鸯针》 第三回 艳婢说春情文章有用 船家生毒计甥舅无知
作者:华阳散人《浪淘沙》:
花月一时明,柳眼青青。佳人有意伴孤灯。琅玕\偷赠相思夜,带绾西陵。香云笔墨生,龙头老成。故园松菊暗销魂。等得他年风雨静,筠柏双清。
却说那卢公子着实看顾徐鹏子,时常梯己做些衣服与他,逢时遇节另有厚赏。鹏子得了安身之所,又有些书籍看,到也忘记了日子。 那一日陈先生不在馆,公子回家过夜,在同娘子吃夜饭。
公子对娘子道:那徐鹏肚里到通,做得好文章,又写的好字儿,这蛮子不象个下流的。今日先生不在,叫人拿些酒赏他吃去。”
娘子道:“原来恁样。”就叫身边一个丫头叫做飞鸿,“你将桌上菜拿两碗,酒拿一壶,送去书房与那徐鹏吃去。”飞鸿应了,想道:“甚样一个徐鹏,相公这等夸奖他?等我去瞥他一瞥,看他是怎样嘴脸。” 飞鸿拿了东西,一路来到书房,叫道:“徐鹏,徐鹏。”
鹏子答应了。飞鸿道:“相公叫送些酒与你吃,来接去。”鹏子连忙出来接了。飞鸿暗道:“原来徐鹏也还好个模样儿,到象斯文出身,不似家里那些人粗头蠢脑的。我想娘子房里几个用人,都招了那些夯货,我若招得这样一个人,死也遂心了。
不如先勾搭上了他,叫他对相公说情愿要招我。相公是心爱他的,料想必肯。”心意已定,只相机而行。正是:未遭青眼文章伯,先透朱衣鉴常旨。
打听那一日公子往那王年伯家吃酒去了,飞鸿寻出一对戒指,一枝耳挖,一条绉纱汗巾,一总包将起来,自家掠掠鬓,抿抿头,走到书房来。但见他:头挽乌丝,面涂红粉。身着青衣,裙布荆钗无赛;腰缠罗帕,春葱弱柳堪怜。两脚不大不小,高底红鞋;半臂非旧非新,镶边绢面。虽不是玉楼上第一佳人,却也算香阁中无双使女。
飞鸿轻轻的走进书房来,只见鹏子在那里写字。鹏子道:“飞鸿姐,你来做甚么?”飞鸿道:“相公不在家,我来顽耍一会儿。”就两手伏在鹏子桌案旁,看他写字。飞鸿道:“你的字到写得精致,不象相公的,一个大,一个小,七歪八扭的,怪道相公欢喜哩。”又问道:“相公今日王家吃酒,甚时节才回?”鹏子道:“大人家酒席,那里就散?要回也要更把天气。” 飞鸿道:“相公不在家,我替你做伴儿可好?”鹏子道:“这个不敢劳。”飞鸿看见架上四季盆兰盛开,他就走去,折了两枝。一枝插在自家头上,拿一枝走进来,替鹏子簪在髻上,道:“好香花。”鹏子道:“不要乱摘,恐相公回来嗔怪。”
飞鸿道:“你放心。有酒不饮是痴汉,有花不采是呆人。”
他见鹏子只管写字,全不照他,他便走上前将鹏子背上捏了一把,道:“你不怕冷么?相公昨晚对娘子说,要买布做件棉袄与你穿,你这蛮子到造化哩!”鹏子道:“这是相公恩典,有甚造化不造化?”飞鸿道:“徐哥,我有件人事送你,你好些收着。”鹏子接过一看,见是那三种物件,就依旧放在桌子上,道:“你还拿去,我不敢受。我也无处收放,恐相公娘子查出不当稳便。”飞鸿道:“这是我梯己的物件,怕他则甚?
你若说起相公,相公到好巧主儿。娘子房里头几个用人,那一个不摸摸捏捏的?偏见我不肯如他的意儿,所以娘子单爱的是我。徐哥,不瞒你说,你有甚事儿通知了我,我去对娘子说,看有那件不依。”鹏了道:“我也没甚事敢于烦娘子里面,”飞鸿道:“些小物件不肯收,当面来怪人。”就故意走近前,将那包物事拾起来,一把手就抱住了鹏子,这只手将那包物事往他袖子里乱塞,趁势儿捏了几把。徐鹏子反不好意思,只得走了起身,道:“尊重些,恐怕老爷晓得,问罪不便。”飞鸿见他不知局,一骨碌睡倒他床上,口里哼哼唧唧,唱起俏冤家来了,徐鹏子见他皮缠不过,没法儿打发他出去,又怕人来撞见,故意道:“几乎忘记了,相公曾叫我在书铺里取书去,我要出门。飞鸿姐,你一个儿坐坐,还是怎样?待我好锁门。”
飞鸿见不是知音,只得爬了起来,拾了那包物件,藏在袖里道:“恁呆忘八羔子!送你的东西不要。”才出去了。这正是:坐怀不乱柳下惠,见物不取杨四知。
流水落花消息杳,清天明月显心期。
却说那一日按院到了,要观风。学中领了题目,送来与卢公子做,又是徐鹏子代做了去。原来那按院与卢翰林同年,一见了公子这卷,大加称赏,拔取特一等一名,将文字发刊了,又备了一付礼来拜卢翰林,极口赞诵公子的文字。卢翰林道:“小儿谬蒙称许,其实过夸。忝在同年情谊,还求直教才是。”
按院道:“小弟非面谀,令郎才气,实是北方翘楚,将来决是英发的。恐怕小弟的批阅,还称诩不荆年兄试取一观。”
就叫人送上那观风全卷,亲手揭那两篇,递与卢翰林。卢翰林一看,果然比往日所作不同,暗自诧异,却又不好自家夸奖得,只得道:“略称题情而已,怎么当得年兄那般赞扬。”作揖谢了。从此以后,凡遇月课、社课、各台观风,但是传题目来做的,没有一遭不是卢公子一等第一名。快活煞了一个卢公子,又快活煞一个卢翰林,并快活煞一个陈先生。两个人只道公子鸳鸯针·0·用心攻书,文字骤进,那里疑心别样的缘故?恰是:竽与瑟混他一场,鲢共鲤谁分两样。 恰好那几时提学道来岁考,卢翰林要打发儿子去考,治酒饯行,极其隆盛。又送许多脩金、盘费与了陈先生,叫他相伴儿子。陈先生得意扬扬,摩拳擦掌,极口道公子此去,定又是个一等一名,不消说得。卢翰林心下信了,难道口中还好说未必?只说道:“谢先生教导之功。”那晓得考过了不上几时,就也发案。看案之时,只见卢公子高高考在五等,这五等或者还是提学奉承他令尊的;不然,恐怕六等也就要见教了。卢翰林大怒,呼拿文字来看,道:“这样文章考五等不枉你。为何那日做出这样文字来?”公子道:“那日心下不自在,故此胡乱做了,完场而已。”卢翰林道:“岂有此理!心下不爽利,或者机括不顺,文采不甚发扬些,那里天渊悬隔若此?这事我决不肯信的!”这正是:文章自古有凭据,莫教雷轰荐福碑。
卢翰林心疑不决,走到馆中对陈先生道:“以儿昨日的考卷,应考那等数上。只是前日那几篇观风社课,何处得来?大相悬别,遂尔如此?”陈先生道:“正也在此委决不下。小弟有一计,每逢三、六、九,便是文期。明日该做文了,午间屈老先生过来,面看他交卷,是非好歹,顷刻分明了。”翰林大然其说。
次日,果然不等午后,就过书房中来看公子誊清,将文字来大家看了,却又是好的。卢翰林道:“这样文章还有甚话说。
为何岁考场中不写出来?”陈先生道:“文字有一日长短,令郎道那日不自在,或者果然。就今日这两篇看来,还是令郎天资颖悟,闻一知十,故尔骤进。终是老先生家风水气运,应得科第蝉联。小弟面上,预有荣施了。设使今日这两篇文字,还学那岁考场中的,不唯老先生扫兴,连小弟在此也坐不住了。” 卢翰林虽然点头,心下终是狐疑。毕竟他做官的人精灵,见识不同,心下想了一想道:“有理,有理。”
次日坐在一间楼下,叫人去请大相公来。公子被唤来到。
翰林道:“楼上有个题目,你上去做一篇文字我看。”
公子不敢不遵,随即上楼。卢翰林已自将那楼门下了锁,钥匙带在身上。稍顷,午间又亲自开门,看丫头送饭上楼,下来依然锁了。这正是:不是棘围严弊窦,也将家法整文规。
公子上得楼来,见楼上并无一物,止有笔砚一副,竹纸数张,“四书”一本,题目一个。公子道:“这遭着手了。”不敢有违,只得磨心镂肾,下力去敲推一篇文字。从早晨做到日晚,还要点烛上去,方才写完,亲自交了卷。卢翰林看了道:“这篇文字与那岁考的差不多。”因笑了一笑,点点头道:“这等看来,你前头那几篇文字,当真是抄写的无疑了。今后你也不必读,止学抄写罢!”公子会意错了,只当说的抄写,就指了徐鹏,前头事父亲已晓得了,不觉的自家招供道:“前头那几篇文字,果然是那抄写徐鹏的。”翰林大惊道:“是徐鹏做的?”公子应道:“是。”
翰林就叫人去叫那徐鹏来。那些人那晓甚着数,闻命一片声叫喊:“老爷叫徐鹏!叫徐鹏!”到把鹏子吓了一大跳,道:“老爷叫我则甚?”那些人道:“大爷前日的文章,说都是你做的,故此叫你去。老爷发性哩!你去讨仔细。”
鹏子暗道:“这事决撒了,怎么样处?”又想道:“场中倩代,怕有罪犯;这私下何妨?难道也问我的罪不成!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,怕不得这许多。”就同了众人来见。
翰林道:“你也做得文字么?”鹏子抬头见翰林颜色甚和,遂应道:“也胡乱做得几句。”翰林道:“果如所说,楼上现有纸笔,你就将今日的题目做一篇来我看。”鹏子领命,不上一个时辰,早已写了一篇,呈与翰林。翰林看毕,道:“果然不差。你做得这样好文章,决不是风尘中人了,可实对我说,我自然奖拔你。”徐鹏子始将真姓名来历,并革黜落难前后事说了一遍。卢翰林道:“既是如此,作揖请坐。明日就同小儿一起读书。兄有如此抱负,勿忧贫贱。 向来失赡之罪,万望容耍”次日盔了一顶巾儿,又做了一身衣服与徐鹏子换了。家下人俱呼徐相公,不是甚徐鹏徐鹏了。那徐鹏子也感激翰林知遇,时常将南边风气派头,极力诱掖公子。公子受了这番耻辱,也用心揣摩。不一两月,公子果然文章骤进,不是训谎了。这正是:鸢肩火色偶飘蓬,昨日侪奴抗衤乇翁。 不是一番寒透骨,居然千里骋追风。
却说徐鹏子离家之后,倭寇作乱,浙江一带地方,并无宁宇。经过地方,鼠逃鸦散;未经过的地方,鹤唳风声。大小男妇,东边的走到西边,西边又走到东边。山谷之中,啼号不绝,所在地方,皆负担载锅而立。这样流离奔走之苦,真个说不尽的。那鹏子浑家王氏,穷到那等田地,那里还有亲戚朋友来照顾他?只得也背了个包袱,同这些男妇,趁伙而走。恰好走到一个所在,一起男妇坐在那里,王氏看见一个人,甚是面熟。
仔细瞪了一会,原来是卫里那个识字。想起来道:“阿伯,你也在这里?”那人道:“你是谁家宅眷?我一时失记了。”王氏道:“拙夫姓徐,叫做鹏子的。”那人道:“原来是徐先生娘子。失敬!失敬!”王氏道:“阿伯也晓得他们一路去的消息么?如何至今不见一封书信回来?”那人道:“娘子,你还不晓得么?说起也是一件新闻。他们粮船到临清地方,失于提防,被火烧了官粮。
闻得运官羁候在那地方,早晚要提进京问罪哩。”王氏道:“这样可曾识得拙夫消息么?”那人道:“这是别帮上人回来说的,恰不识得徐先生的行止,不敢谎说。”王氏道:“这样看来,或者有些长短怎处!运官既问罪,他们有甚事?如何至今不见回来?一定是作他乡之鬼了。”王氏说到这里,也不管兵荒马乱,一顿嚎啕大哭起来。那人道:“也不消啼哭,须得个的实人,打探一遭,才知端的。”
王氏哭着道:“他生长宦门,上无兄弟,下寡男女,一时落薄下来,有谁人肯去打探?除非妾身亲自去才好。”那人道:“你一个妇人,出门甚是不便,我有个道理。这两日有个粮船开帮,管船的是我舍亲,我就去对他说,只要你饭米,不要你搭载钱。共是一块土上人,你便同去同回,这还是可以放心托付的。”王氏道:“千万借重阿伯去说,明早回我一个信儿,这就感谢不荆”那人道:“明早准回你信。”次日,果然那人来回信道:“他日内就开船,你往大埠头舡帮上问李麻子就是。我已与他讲明白了,你快早收拾上去。”说罢去了。这正是:一时无远虑,千里别家门。 前路多风雨,萧萧断旅魂。 那王氏收拾停当,即时找船帮上,问着李麻子的船。李麻子道:“你是徐家阿嫂么?我舍亲昨日说过了,请上船,今日还要开帮哩。”王氏拜谢了。
原来李麻子是个游荡不实之徒,年已三十多岁,还不曾娶亲。只有一位母亲,有六十多岁,带在船上,替他烧火煮饭。
他头日听那识字说,还不知是怎样一个人,乃至王氏到了,见还是位年少妇人,心下想道:“这妇人也还干净,又少年孤身上我的船来,明是天赐姻缘。开船的头一日,就有利市了。弄他上手松松腰,胜似到埠头三钱一夜嫖那歪娼。闻得他是找寻丈夫的,倘或找寻不着,弄得他燥脾,或者长远跟了我,也未见得。瓮中之鳖,怕他飞到那里去,这不是白白得了一个好浑家!”暗自欣喜。当下安他一个舱口,早早晚晚,小心贴意,问茶问饭,好不殷勤。王氏只当他是好人,十分难得,着实过意不去,那晓得他是肚里怀奸诈的。这正是:甜言蜜语休轻听,义胆贞心好自持。
过了几日,众人先睡了,李麻子吃得醉醺醺的唱上船来,竟到舱口问道:“徐阿嫂睡了不曾?”原来王氏自上船后不曾解带,连衣服倒在床上,略歪歪儿。听见李麻子叫唤,忖道:“这夜间叫我则甚?且不要应他,看他如何行止。”李麻子见叫不应,悉悉索索撬那舱门。船上的门是没有拴锁的,一时被他弄开了,他便挤身进船。王氏喝道:“是甚人,乘夜来钻舱?
“李麻子道:“是我。我怜你孤身寂寥,特来陪你睡一觉儿。” 王氏道:“胡说!我是大人家男女,你莫要认错了。快些回去,休要胡行!”李麻子道:“心肝,你上我船来就是个缘法,分甚大人家、小人家,且图快活一宵儿罢。”说罢,就双手来抱祝王氏急了,便跳起身来,劈面就抓打。李麻子终是粗人,气力大,一交按倒床上。王氏叫道:“不好了!强奸良家妇女!
“李麻子忙放了手,来按他的嘴,被王氏乘势一挣,爬到舱口,大声喊道:“救人!救人!强盗杀人哩!”李麻子慌了,见不是局,忙忙的一溜烟去了。王氏待要声张起来,想道:“在他矮檐下,也要将就三分。我来所干何事?万一决撒起来,怎样开交?我只是坚正自持,不怕他怎样了我。待寻见丈夫,再与这厮打话,还是隐忍为高。”当晚就也不则声了,依旧将舱门紧闭,上床暗暗的去哭了。这还是王氏正气,有主意,不然,已被小人玷污。这都是妇人轻易出门之过。这正是:妇人不可出闺门,容易花开蝶骤侵。
古云在家千日好,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到次日,李麻子也觉得自家没趣,茶水上懒懒散散的,也不来周致了。王氏情愿乐得,也不稀罕他。不几日,船到了临清,大家买神福,热热闹闹的。王氏见到临清,对了李婆子说:“阿妈,我上岸找寻一回就来。”同了船上一个小厮,上了岸来,逢店家便问。本地人道:“是有此事。去年曾有一帮粮船,在这里失了火,运官羁候这里半年,后来提到北京,坐通天牢去了。”王氏道:“他船上那夜曾折耗个把人么?”那些人道:“也坏了几个人。”王氏道:“他请一位姓徐的做先生,不知列位也识得他在与不在。”那些人道:“坏了的人还埋在本地,不曾收尸回去。却不知得姓张姓李。”王氏逐个细细盘问,没有一个人识得。只有后来一个老者道:“记得旧年东岳庙里说有个粮船上落难的人,在那里几时,却忘记了他的姓名。
小娘子要问详细,须到东岳庙里访那些道士,才见分晓。”王氏道:“这里到庙有多少路?”老者道:“远哩。来回也有四五里路。”那王氏就要前去,那小厮道:“上来盘问这一会,肚中也饿了,且回船上吃碗饭来,再走这些远路。你又走得慢,来回要好一会工夫,也要上船去支会他们一声。风水地面,不是当耍子的。”王氏道:“说得有理。”走回船上,对众人说了这番话。众人还未答应,只见李麻子跳起来吆喝道:“放他娘的屁!我撑的是官船,装载的是朝廷漕粮,谁人敢道要行要止的?我又不曾得人三厘半分,谁是他家的奴才!莫说大人家、小人家,再要络索些儿,一条绳子捆了,丢在水里去,到海龙王那里告冤状来寻我。老实对你说,我们粮船上人,欠在你恁一条狗命哩。”喝叫把船开了,移在别港去。众人一齐动手,把船脩脩呜呜的开了。气得那王氏眼直白瞪了,有眼泪也淌不出来。此时漫天无际,孤掌难鸣,稀罕你一个妇人?只得眼睁睁看他把帆扯开了去。
王氏到了后舱,来对李婆说道:“阿妈,可怜我同你是一处人,你老人家搭救我则个。”婆子道:“你是怎说?”王氏道:“我原是寻丈夫的,丈夫既不要我寻,难道叫我运粮进京去不成?少不得他要打发我先回去。”婆子道:“你意思是怎样回去?”王氏道:“遇着南去便船,搭他载回去就是。”婆子冷笑一笑,又叹了口气道:“我说你这小男嫩妇家,不知出门艰险,我这船是地头载夹的,还有些抓拿,譬如遇着一个便船,把你送将上去,你晓得船上的人,是那个天南地北的?你一位妇人,安顿在那处好?那船上都是好人。你扯不得个直,万一有个歹人,把你卖了几两银子,送下水去,你在那里去叫屈?出门若是恁样容易,男子汉在家的,也没影儿了,稀罕你是个妇人,没脚的蟹?怪道你少年家不晓事体,一发可笑了。”
说罢,叹了一声,就睡倒船舱板上了。王氏此时冰冷水浇背,一般,才悔道是自家错了,不宜轻易出门。见婆子话甚是有理“我如今没奈何,只得拼却跟他前去,看他怎样好歹,这一江水,是我结果之场了。”暗自流泪不了。这恰是:人情险似太行山,何地羲皇任闭关。
一日风波惊十二,岂徒出外片时难。
却说这些人只有李麻子心里难捱,道:“这雌儿弄不到手,明是一块天鹅肉,忍得到只反吊馋了人。我若是再去麻缠他,恐怕学前番模样,乱起来,不成体面;若丢着不去理他,心下又不肯服气。”终日满肚子打稿儿,又想道:“啐!呆了不成? 不得人也得银,这样人儿到北边少也值四五十两银子。到前路去将他卖了,我有了几十两银子,怕讨不得个小心贴意的!要这样强头强脑的东西做甚么?”心下主意定了,不几时到了天津。这天津却是安泊粮船去处,大家到了这里,都放了心,终日吃酒嫖妓女过日子。正是:满腹思量寻活计,谁知终遇死冤家。
原来前日与王氏同去问信的那小厮,就是李麻子的外甥,年纪虽小,到也乖巧,有些鞋脚都来央王氏替他做。王氏也可怜他,每次顺手就替他收拾停停妥妥的,那小厮甚是感激他。
那一日道:“徐阿妈,我一件衣服在船篷上拉破了,烦你老人家替我补补何如?”王氏道:“你拿来我替你补。”那小厮也就坐在旁边道:“阿妈,阿妈,你一件喜事,你晓得么?”王氏道:“有甚喜事?”那小厮道:“我对你说,你莫对麻子说是我说的。”王氏道:“晓得,你且说来。”小厮道:“我那麻舅舅将你嫁了这里人家。前日上船看米的,是故意装扮来相看你的。看了中意,出了三十两银子财礼。我舅舅要他四十两,熬了这两日的价钱,适才那说媒的又来叫麻子去,在那酒店讲话。约定一面交银,一面抬人。”王氏道:“你怎么晓得?” 小厮道:“我在酒店里问麻子讨钱买菜蔬,就叫我吃几杯酒。 我听得,特来告诉你。
你若是去那人家,须要早些收拾,莫待临期慌忙。只是我一向难为阿妈,没有甚报答你的。”王氏道:“恁样我替你缝衣服,你还上岸去打听。有甚话说,千万飞来报我知得,我有好东西来谢你。”那小厮家晓得甚么,应了一声,欢欢喜喜地飞也似跑上岸去了。
王氏暗惊道:“这个恶贼,这样狠毒!倒是这小厮来告诉我,不然白白的吃他骗了。如今我死在这里,无人知见,也是枉死。这是通北京的大去处,前途自有活路头。我算计三十六策,走为上策。”即忙收拾鞋脚,带了些盘费。此时天已黑了,船上人都上岸吃酒去了。王氏走将出来,四顾无人,三步两步跳了上岸,不往热闹去处,傍河涯冷静一路,舍命奔将前去。
这恰是:
路当险地难回避,人生何处不相逢。